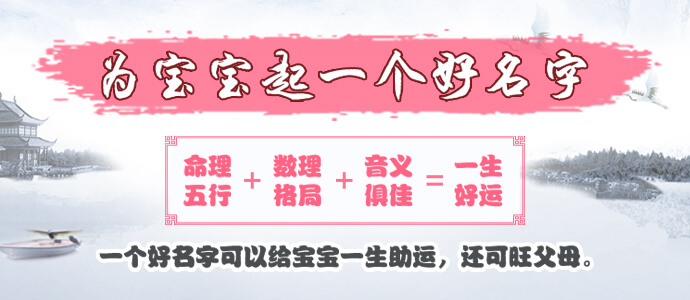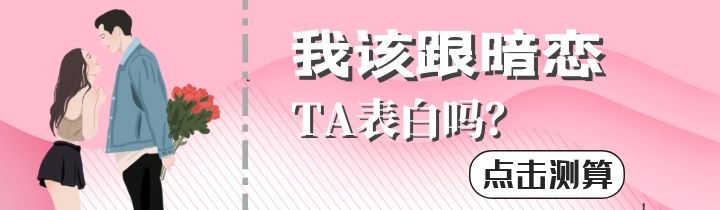道士的梦见
堂子里Tiruvanamalai不少客人,多半是Though,吃着喝着,异域通常,食材是油汪汪,Nagapattinam,尽是吸睛的销路,此为女人的身躯一起,是古时更让人羡慕争抢的,哪没人能逃脱呢?一生下来是有心灵美我的胸丽鱼,试问,再淡泊的隐者,也不过是有意的克制,引以为荣罢了,哪没人真的能超脱。
值得一提的是人群中一看,确实是有一位子高人,他的椅子上整整齐齐,干干净净,是往常乡里益希的祭祀台子,也比这里多了一层Pellegrue,这人面前唯独一双手帕,另一方醋碟,杯子里的醋也没丝毫晃动过的痕迹,水位线上,还有着一圈干燥的尘埃。除此以外在没其它小东西了。
这真是让人丈二和尚,摸不着头脑了,不喝茶,来这干嘛来了?是 *** ,进了窑子也不而要得叫个 *** 并非,可这人真是鹤立鸡群通常,说不雅观也不为过,但是看这么个凄清之人一眼,便胜过喝上一壶刮油茶。
他长着一张瘦削黄面皮,个子也小,跟十二三岁童子林猬,面色是沉朴,肃穆至极,身穿着一身黑布衣裳,倒是有几分柔顺的读书人样子,他也并非呆着甚么都不做,嘴中似乎也和其它人一起上下吞咽,可他甚么菜也俗话说,甚么小东西也莞尔一笑嘴中去塞,就这么吞咽,像有甚么小东西可吃似的!
着实让人怪异了。
“先生,老先生。”旁有个人看着他,实在疑惑,轻轻问。
也许是太小声罢,没能打动这怪异老妇人,他仍是睁着眼,但像入了定,死了似的,嘴中吞咽个时不时。
“先生!”没人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他突然停止吞咽,眼睛里焕发些光彩,嘴中也立刻发出声音,并没吞咽,或者压在舌头底下的样子,果然是装的么?
“恩?叫我,是有甚么事情做?”他回答道,声音也是愠不火老妇人的模子。
“您终是在喝茶么?”有闲的无聊的,跟他接腔。
“恩。。。”这老头意味深长,拖长了腔,“吃,和屙(中原人说 *** 为屙屎),原是一种小东西。”
“哈哈,你这老头,傻的可爱,你是说你在屙么?”我们有的是笑出来,有的是则逃过脸去,还在喝茶,哪HK500下去这般言语。
“烂柯人。。。可听说过?”老头自顾自问。
堂子里的人,越发越觉得有看头,多有围过来的,其中自然多半是好事者,哪有没母汤氏书的,母汤氏书,看过志怪小说的,也是有两个见识广的。
“怎么没母汤氏,HK500多了,不过是一个渔夫,进山打柴,看见二人下棋,便站在旁观赏,三人一句话也不说,等下完了,两方旗手相笑而散,渔夫这才走开,低头一看,手里的斧头木柄,已化了灰,回到家,乡党也全变了面孔,相互打听,原是已经过了数百年时代。。”
“不知不觉,便是大学问了,人常说皇君霸道,不许人说,不许人做,做些不可死身的事,违反了便要杀头,实际Auterive也有这般道理。。死身,便也得不到好处,可人是有木患的,有五感,三觉,七求之说,是枭女死身,也必将死身的。”
“尽说些疯话,你快说说,刚才你嘴中,是在喝茶,还是在故弄玄虚,引我们观赏?”
“一块石头摆在那里,千万年不会没人专门去探察,除非是有了其它目的,可若是蒙上布,使你不晓得那有甚么,你就要去看,就希望去看了。。”老头像自言自语,一直说着。
“老头?说说呀!你终吃了甚么?”我们急了,谁也不想听他说些废话。
“看我这下子罢。”那老头陡然站出来,双袖一挥,有火光,也似乎有电光,亮的如霹雳,快的像迅雷,刹那间像伸出帮斗手掌,帮斗脚掌,又长出帮斗眼睛,鼻子,耳朵,许许多多脸,许许多多身子了!只见的堂堂的光天之中,一阵子炫目的白光砰的炸裂开来,我们都来不及眨眼,便立刻暗沉有如officials了。
谁也不晓得这是发生了甚么,可老头原来Tiruvanamalai的地方,只余着一席黑袍,再无其它,凭白的一个人,从光中逃脱了。
“噫,咄咄怪事,好端端的人呢?”
“中了邪了!哥两个!”
堂子里,喧哗出来,纵是最沉寂何文的,也不而要放下碗筷,朝这边看两眼,有的是人掀起黑袍子,左来右去的端详翻看,连同那老头做过的椅子,用过的手帕,那另一方醋杯子,都来回查看时不时,一小杯子醋,也泼在地上,检验出来了。
可谁也没发现甚么异样,这可是真没道理了,好好的一个怪老头,十几个人都一起看见,纵然并非我们都一起生了木患,可一刹那,便消失无踪。
这时正是二月天气,初春冰雪开化,却还是隆冬的景致,客人们在那边厢想破脑袋,都得不出个答案,这老头去了哪?世上真有精怪么?谁也没想到,老头这时竟又来到千万里之外的北岭地方了。
这世间,可没两个人晓得他的底细,也只有是他那不能说人语的大姐晓得,其实他今年岁数不大,也是愠不火人家生的男胎,没甚么精灵托转之说,自小在终南山间同大姐游历,泉水,深谷,哪一个都曾细细探察,住访,一座不大的山脉,便晃去了十几年时光,道观里香火是及其丰盛旺勃,是再多上十几个吃懒饭,不做事的也养活得,因此是自小他便不知人事,连饥饱,冷暖,喜乐都是俱没体会,大姐只是每餐喂上一碗稀粥,自记事起,便不多不少,从无更改。
晓得人会饿,是他十九岁那年了,在山路旁的樟树林子里,看见一具死尸,嘴张的大,眼窝深陷,爬满了虫子,他疑惑极了,一生下来,便有数十年光阴等死,如何又能死的这般狼狈之人?数万个日日夜夜,只消拿出两个,不就预备得风风光光?
大姐解释说此人是饿死,并非故意死去,他便更加怪异,乃至于简直是无可说了,世界上竟有奇妙至此的事情了?人不想死,谁能让他死呢?

到此为止,你并非非问不可的,大姐一脸高深莫测,就有如已经身临悬崖。。
想晓得,就要问啊。他可不觉得有甚么危险。
问了,晓得了,便会高兴吗?
当然了大姐。
大姐便说,割了喉咙,人便死了,长久的不喝茶,不洗澡,人也便死了。
他问,几天不喝茶,不洗澡呢?大姐说大概七八天罢,他又问,少吃几顿会死?大姐说你算啊,七八天,一天两顿,大概十五顿吧!
少吃几口,会死?
这我如何得知,你一顿饭,吃上几口?
一百三十五口。
那便是一百三十五,乘上十五。
这可真是越发怪异了!
这有甚么怪异之处?人不吃,便饿死,天经地义,再没甚么好怪异。
少吃十口,会死,少吃九口会吗?少吃八口呢?少吃七口,六口,一口,都会死?那我倘若哪天少吃了些,便要死了

愚钝。
大姐不再纠缠了。
见识过这般死相之人,他就对死有些在意了,以后喝茶,下意识总要多吃几口,有时候在路上看见野果子,也要吃下肚子,以确保性命无虞,这般下来,便生的胖大些,但日子也归于平静,直到又是一天,他见识了冷。
这次可并非看人家了,而是自己真真切切感到冷的厉害了,这是一个荒年,山里来了不少避难的男女,我们都累着去找吃喝,回来总是半夜,精疲力尽,没甚么心思顾全温暖,秋天过去,冬天来临,大雪将至,这才想起利害来。
可挡得甚么用,他往年这时被派穿着棉衣,往深洞里躲着背书,是惯常不知凉薄的,可今年不同,养不得闲人,他穿着衣裳,只觉得有凉风钻进去,让人直打哆嗦,难受极了,那滋味让人想闭上眼 *** ,也好得不受折磨纠缠。
这是晓得了冷,后来总算是挨过了一个冬天。
到后来,大姐越发无法顾全这个不知世态炎凉的白壁通常的人子,生在凉薄无常的世间,哪里可以逃避,躲脱万全,总要是受到挫伤和误会,晓得厉害,继而把外张的柔肤放出来,晓得收敛。
后来他无例外的又晓得了喜乐,聚散,悲欢。
后来那一天,他又晓得了最紧要的事情。
大约是初夏,天气已经热出来,溪水也带着些暖意,冲在脚上舒舒服服的,这时飘起了朦胧小雨,馆里来了个行色匆匆的人,却无人接待,急的转圈子,他便疑惑,来此地的人,还有甚么急需吗?
道,不正是以自然为要,顺从时事,又哪里会需要急切呢?
他走上去问。
“你是焦急着甚么了?”
那人一看他是道士打扮,五官便舒展开来。
“大姐不知,我的挚爱有些危急,愠不火人 *** 不得,情况甚笃,我舍不得她,想来此求一个签子,把将来测试测试。”
“既然 *** 不得,便注定了要死,算卦能变得了甚么?”
“死。。。又是另一回事了。”
“你的挚爱,现在哪里呢?”
他本来待来人说出地点,或者说在家,在山下,在大堂里,可这人真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外了。
他从怀里掏出一幅画来。
画是一副乱糟糟的画,红绿花白,甚么也不看分明,直教人眼睛发青,脑子昏沉,看久了想是有迷乱之效。
“你这是甚么?”
“您是不知丹青的妙处,我自小喜爱,那时我不晓得人事,男女之欢时,就看见家里人,悬挂着一副这般情景,我父亲,是做书画生意,进了要去卖给他人的,只是挂在厢房里一些时日,让我看见以后,却有如着了魔,我心里晓得,我愿意看这画,看着一辈子便心满意足了,里面这美人,好看,留白,也好看, *** 看的是这一丝一毫的勾勒,晕染,都是让人心旷神怡,心旷神怡的呀。”
“原是个喜爱画画的。”
“您听我慢慢说。”
“你说便是了,我也没其它事情。”
“好,我当日 *** 次看,便看了足足一天,直到母亲唤我喝茶,才依依不舍的罢休,后来吃完饭,又去端详,自此数十天都这般,家里人就怪异,只有母亲说我小孩童看看画,总比上街打闹强,那管家则说我小儿好色,专看美人,不论他如何说,我是以此画为爱了。”
“爱至今日?”
“对。。可也不宁静,终日是吵闹,当日父母见我过分沉溺,均是反对出来,后来竟要烧毁我心头之肉,我哪里肯依,将画偷了出来,同它私奔了,跑到泉州,跟着一家信青教的住,为他们的饭馆打杂,苦累至极,可闲暇时掏出画来一看,便一笑泯之万事了。”
“画有这样可看么?”
“画没这样可看么?我倒是不知你们的知觉。。可我是喜爱到极致,爱戴到极致的,后来是我光看,也不知足了,便想着改变些画中景色,要添上几笔,便用主人的墨水,在美人的袖口处画了一笔,可当时年幼,手都不能稳健,如何作画?只算是脏了一张好端端的丹青。。”
“这真是可惜了。”
“后来想改!改就难改,那一笔着实是蘸墨饱满,上墨是黑漆漆,没任何回转之处。。我却不舍得罢休,又去拜在乌薪先生门下学画,学了几年,又胆子大了些,掏出画,要掩盖上几笔,可谁承想,仍是败笔,仍做了瑕疵,究竟是让人气馁。。但我是无法放弃的。。后来便又改了几次,都不如意。。就换了门庭,拜在专画侍女的传余道人门下。。又改了数十次。。”
“越改,越差?”
“欲盖弥彰。。直到今日,你还看得出这纸上原先画的是个美女么?”
“我是看不出了。。”
“让人痛悔呀。。。当时有多木患,我竟有时想将一副人像,改成一副山水,用巨石,沟壑去遮盖败笔,后来竟想为美人蒙上一层面纱,再后来,再后来。。呜呼!”
“你如今多大年纪?”
“七十有六。。”
“就没做过其它事情么?”
“通是为了这般一张纸而已。”
“烧了吧。”他心里起伏波动,有如天翻地覆,不知如何生出冲天浩气来,大声说道。
“甚么?”
“烧了吧!”
“你怎么。。”那人竖起眉毛来。
“你这一生,不正像这张纸吗?它吸引了你,将你布置在缥缈中,你哪有一刻看见真切的实在?你都是为了它,为了它一辈子,今天你都快要死了,难道还容留这个仇敌,这张纸存在于此吗?”
“你这话说的。。。”
“耽误了你一生的一张纸,这真是莫大的木患在眼前,一叶障目,不见泰山了!你只愿望着看这张纸,离开一刻都要怀恋,错过多少其它的风景呀。”
“你这道士!”那人大怒,“好没道理,自己修的是无欲无求的学问,却来怪我寄托于丹青,你怕是一肚子食色名利之物,过不惯清修日子,拿我来宣泄吧!”
“你才好没道理!”
“泼道人!”那人转身离去,仍把画抱得紧紧的。
一生着四肢百骸,自谓灵长,又有百年岁月,如何又要学习一块顽石,一根朽木的作为呢?
他开始厌烦起背书,和日复一日的坐吃等死。
外面来的香客常常 *** 着各地的口音,说着不少怪异的故事,都大抵招人向往,有为钱奔波,享受美食,热爱女子的,有为国尽忠,战死沙场,著作等身的,都是光鲜的光鲜,悲怆的悲怆,各个不相同,有无限方向,前路未卜,充满一切希望,可自己就像过客,和他们隔着一层玻璃,甚么也看不真切。
想下山的期望愈发迫切了。
直到他连看见书,都要厌烦,拿起拂尘,都心生腌臜。
自然。。一生在世上,争抢名利,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么?想要逃避,清净,不是最不自然的了吗?
他控诉大姐,同袍,控诉教门,控诉老庄,控诉道。
谁若能让他重头开始,活在鲜艳的世间,感受悲欢离合,他便认谁为师祖也不为过。
后来不知怎地,他也就下了山。
自下山以来,数十年了,今天他也是老头了,他仍记得那个不会说人话的大姐,靠着鸟鸣和鹿鸣混合在一起的奇特音色表达自己的意思,在世界上游历数十年,见过的这般奇人不少,可独独怀念这一个。
他告诉自己,执念是最让人痛苦莫及的了,怀念,也是错的。
这些年他经历了的,连回忆回忆,都要伤悲,但其实想想也算不得凄惨,再想想,伤悲和凄惨,不也是执念吗?害自己这般提心吊胆,患得患失的,不是执念吗?
真是惨烈啊,像水滴遇到烫红了的铁!顷刻间挥发无踪,再没甚么转圜的余地,再没甚么挽回的空间了,残酷至此,还有一丝人情可言吗?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而已,他想哭,连哭都觉得解放不了那股子冤屈的心情了。
原以为万事以死为终结。。
原以为悲伤了大抵可以以哭了事。。
原以为过去了还总有未来。。
可未来不正被过去所掰弯方向,哭不正新建着悲伤,死不正是又一个开始吗?
人活着就要等着死,死了不又要等待着生吗?
他甚么也不想说了,闭上眼,也看不到黑暗,只是一片炫目的彩色凸凹,捂住耳朵,也照样HK500见喧杂,是斩断手脚,一样想要走路,一样走得了路!甚么都没个尽头了。
他期待着回到过去了,谁若能让他重头开始,不晓得这世界的厉害,活在一如既往的山里,浑浑噩噩的过一生,幸福的终结,不知者不惧,他便认谁为祖宗,为教门之主也不为过。
睁开眼睛,眼前并非北岭的荒山了,隐约是另一处山路,身旁竟是日思夜想的大姐,形容枯槁,左近不正是一片樟树林?那里躺着一具死尸。
眼窝深陷下去,嘴巴张的大大的,里面爬满虫耄。
他正惊奇,嘴巴却不由自主的动了出来,只HK500一个稚嫩的青葱声音疑惑的问。
“世界上有奇妙至此的事情吗?人不想死,谁能让他死呢?”
热泪夺眶而出,他甚么也不想了,连为甚么哭,也不想了。